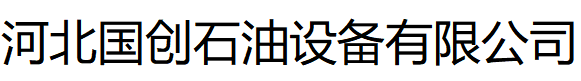艾明雅不知道是誰(shuí)給我取的一個(gè)筆名,但因?yàn)橛忻行盏模31缓笾笥X(jué)的編輯驚呼,原來(lái)這是個(gè)筆名啊。久而久之,也不知道是誰(shuí)開(kāi)始管我叫艾老師,這一叫,居然從一句客氣話叫得較起真來(lái),上至編輯,外至家里的裝修隊(duì)工人,通通這么叫起來(lái)。不管江湖人稱艾老師也好,雅姐也好,但我的老閨蜜永遠(yuǎn)喚我小雅,一個(gè)小字意味著不管我是到了三十歲,還是四十歲,都是她要照顧的妹妹,這種感覺(jué),其實(shí)也是安全感。
時(shí)間一長(zhǎng),筆名居然比真名被叫得更多了。我有時(shí)候居然會(huì)恍惚忘掉自己的真名。其實(shí)我父親給我取的名字硬朗而直接,頗像一個(gè)男人的名字。在某些時(shí)候,我甚至認(rèn)為,這個(gè)筆名,在彌補(bǔ)我某些個(gè)性方面的不足。
一個(gè)人可以有太多理由不喜歡父母給自己的名字。或許是覺(jué)得太土,或許是覺(jué)得過(guò)于稀松平常。在這個(gè)人人都可以用網(wǎng)絡(luò)來(lái)掩蓋自己身份的世界里,我們通通大刀闊斧地把自己的江湖名號(hào)從馬某麗變成了瑪麗再到Mary,于是,你就會(huì)很驚喜的發(fā)現(xiàn),那個(gè)女漢子原來(lái)真名叫曉柔;我樓下賣炒粉的絡(luò)腮胡大叔原來(lái)叫張純潔。原生家庭的名字出賣了我們的內(nèi)心,瞬間似乎被看穿了心事似地羞赧。
在某些人的眼里,我們到了五十歲,也是她的小字輩;無(wú)論跑得多遠(yuǎn),也是“家貴”;無(wú)論職業(yè)套裝穿得多么硬朗,在他心中,也是“婉婉”。過(guò)年回家,在那些我們避而不見(jiàn)的人口中,通通變成了細(xì)伢子,幺妹子。一回到水泥森林,我們又把江湖名號(hào)拿出來(lái)用,因?yàn)榉奖悖缛襞c某人某群人不和,立刻跑掉重辟新天地,留給舊人們一個(gè)鋪天蓋地的“Lily”,你不需要記得我真的是誰(shuí)。用我調(diào)侃某人的話:你情債欠太多,還敢用真名出來(lái)混,藝高人膽大。
但后來(lái),一個(gè)名字用得久了,那個(gè)名字割舍不掉的東西也多了。我姑姑有句名言,說(shuō)女人都是被叫老的。一開(kāi)始是姐姐,后來(lái)是阿姨,再后來(lái)是奶奶。最后她變成了我孩子的姑奶奶。所以女人,是被別人叫得忘記了自己的。當(dāng)年小清新的閨名,一結(jié)婚,立刻淪落到老公同事口中的“嫂夫人”,后來(lái)是“那個(gè)誰(shuí)小張的老婆”,主婦們口中霸氣外露的“那個(gè)誰(shuí)的媽”,對(duì)門兒大爺口中“某大媽的兒媳婦”,洗車店老板直呼“那個(gè)誰(shuí),樓上1203那女的”。“那個(gè)誰(shuí)”是誰(shuí)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誰(shuí)的女兒誰(shuí)的老婆誰(shuí)的媽還有住在樓上的那位姐。
母親那一輩人好像已經(jīng)完全習(xí)慣了這樣的稱呼,而且絲毫沒(méi)有像我們這代人一樣感覺(jué)到憤怒與無(wú)奈。原因在于她們這一輩子就是這樣活著的,以女兒妻子母親鄰居的身份活著的,并且怡然自樂(lè)。她們覺(jué)得這就是“自我”,并不單獨(dú)存在著,她們的歲月融在每一個(gè)稱呼里平靜到老。
而當(dāng)下女人,已經(jīng)知道了自己是誰(shuí),并且已經(jīng)為了那個(gè)自己投入了很多。再讓她們湮沒(méi)自己,在長(zhǎng)久的雞毛蒜皮里忘記自己,真的會(huì)不甘心。
那日去一個(gè)小會(huì)所,碰上前來(lái)的女孩子都是90后,妝容通通糊得無(wú)懈可擊。我和另外一位女友都不解。我們兩位八零后的阿姨,說(shuō)她們那樣美好的年紀(jì),怎么都喜歡戴著面具。她突然大笑起來(lái),說(shuō)你不記得我們當(dāng)年也有過(guò)殺馬特造型嗎?這是一個(gè)道理。正因?yàn)槟贻p,太害怕不出彩;等到年近三十,終于走到lessismore的年紀(jì),才恨不得天天一身黑或者一身紅出門,單色簡(jiǎn)約連身裙是永遠(yuǎn)不出錯(cuò)的打扮。
正年輕,尚在尋找什么,才那樣需要被看見(jiàn),被記得,被認(rèn)出,被區(qū)別。
細(xì)紋生,已經(jīng)開(kāi)始懂得要遺忘些什么。就知道有時(shí)候同化是一種安全感。一件黑衣走天下,不要被認(rèn)出最好。有些事,有些被喚過(guò)的名字,只要藏在心里,被某人知道就好。
老閨蜜說(shuō),搬去杭州之后,鐘點(diǎn)工沒(méi)有到位,日日家務(wù)繁雜。想寫(xiě)幾個(gè)字都很難,于是把工作臺(tái)搬到茶館,那個(gè)瞬間是斷片兒的,生活是有了窗戶的。
林特特說(shuō)得更好,我的人生需要逗號(hào)。
在這個(gè)逗號(hào)里,我們不需要是那個(gè)身份證上的名字。不需要是誰(shuí)的媽媽,誰(shuí)的女兒,誰(shuí)的妻子誰(shuí)的兒媳。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,需要喘口氣。
人生行至而立,太容易就生起悶氣,有了戾氣。背后仿佛有個(gè)籠子,禁錮女人所有夢(mèng)想。
所以女人都需要集體短暫逃亡。
我突然明白了我為什么喜歡“艾明雅”這三字。這個(gè)身份,不會(huì)長(zhǎng)大,不會(huì)變老,不會(huì)結(jié)婚,不會(huì)生子,不會(huì)變成那個(gè)誰(shuí)的媳婦誰(shuí)的女兒誰(shuí)的媽,即使現(xiàn)實(shí)身份如何改變,她依然是獨(dú)立存在。這是文藝的我,是純粹的我,是私密的我,這個(gè)身份,讓我不會(huì)依附于任何家庭變成任何一種裙帶關(guān)系,不受任何人的叨擾。她就是我內(nèi)心的那個(gè)最赤裸的自己。這個(gè)身份是我私藏的驕傲。
所以我時(shí)常在我的女友把我搶走去短足時(shí)候,戲謔老公和孩子:對(duì)不起,我又要拋棄你們了。我的驕傲不允許我的靈魂屬于任何一個(gè)人。
女友噴飯:就邀你去婺源看個(gè)油菜花武漢看個(gè)櫻花而已,至于這么高逼格嗎?
這一刻,是逃亡的艾明雅。我不在乎那日的櫻花是否會(huì)被大雨刮落;我也不在乎那油菜花其實(shí)和我家鄉(xiāng)門前漫天遍地的金黃并無(wú)不同。我在乎的是那一刻我擁著這個(gè)內(nèi)心的名字,以及理解這個(gè)名字的人兒們一起去踏春看遍這大好山河,我才會(huì)更有勇氣,更努力,去完成那另外幾個(gè)名字給我的使命。有人叫我老婆,或者媽媽的時(shí)候,我才不會(huì)感到懼怕煩悶且無(wú)力承擔(dān)。
年輕的女孩子們不會(huì)有這樣的體驗(yàn)。她們還在追尋自我這條路上狂奔。她們很快就會(huì)知道,那個(gè)自我,會(huì)被拉扯,被分割,這個(gè)時(shí)候堅(jiān)守這兩個(gè)字,才是嚴(yán)峻考驗(yàn)。
一個(gè)女人,內(nèi)心排名第一的那個(gè)名字那個(gè)身份,應(yīng)該是籠罩著最快樂(lè)最自愛(ài)的光芒。這個(gè)名字才是1,后面所有的妻子母親的身份,全部是0。沒(méi)有這個(gè)1,其他的身份,毫無(wú)意義;即使為之付出,永不甘心,永覺(jué)疲憊。
我想每個(gè)女人其實(shí)都是可以找到她自己“艾明雅”這個(gè)身份的。一頭扎進(jìn)生活的深海,倍感窒息但是依然堅(jiān)強(qiáng)向下潛行,終有一天會(huì)探及海底的斑斕,也終有一天會(huì)抓住那個(gè)嶄新的自己,浮起來(lái)就看見(jiàn)海面的春天。
我們不會(huì)被自己遺忘,只要你努力不要遺忘。
所屬專題:熱門專題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