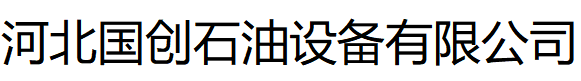這是去年的事。父親住進(jìn)知多半島師崎的醫(yī)院,一個月后父親的病幾乎已經(jīng)完全好了,于是我和母親一起租了一個房間,過著自炊生活。我在距醫(yī)院三百米遠(yuǎn)的地方租到了安靜的房間,只有三餐到父母那邊去吃。
這市鎮(zhèn)是名古屋附近的人避暑避寒的度假區(qū),但不像東京附近的海岸那樣華美庸俗,顯得質(zhì)樸平和,我很喜歡。我當(dāng)時身體不好;并不覺得什么地方特別不適,只是身體非常虛弱,容易疲倦。醫(yī)院病人在海風(fēng)吹拂下,多半膚色黝黑,我蒼白的臉色反而特別醒目,看來我比他們更像病人。
一天午后,我從岬角俯視師崎鎮(zhèn)良久。小港中,漁船猬集。天氣晴朗,閃耀著明亮的碧藍(lán),回映初秋的陽光。我認(rèn)出了曲折的海岸線和大海的色調(diào),以及海岸線邊小小的家屋和家屋后面的綠色丘陵,還看到傾注在這一切之上的陽光,更在這一切之中看出一種難以言詮的和諧,我真想畫一幅很久沒畫的圖畫,在心中構(gòu)思起鳥瞰圖。
我看見一個人從相距五六百米的醫(yī)院走廊走到海岸的砂丘上。我立刻知道那是我父親。父親站在岸上,手擋額前,以防眩人的陽光直射雙眼,一面望著這邊。我以童稚的喜悅守望著父親的行動。父親佇立一會,揮了揮手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我也揮手回應(yīng)父親。父親又消失在醫(yī)院中,我走下丘陵,沿著海岸回去。
突然看見一塊崖崩滾滾的巨石落在路邊,我停下了腳步,仔細(xì)觀看。這時,父親突然從我背后發(fā)出聲音。我起身拂去手上沙子,回過頭來,父親快步走到我身邊。
“喂,有什么事嗎?”父親急步走來,喘著氣,很擔(dān)心地說。
“沒有。”
我對父親的問話訝異得睜大了眼睛。
“那就好……剛才就很擔(dān)心,深怕你站在懸崖上,暈眩掉下來……你本來就常常會發(fā)暈……”呵,剛才父親從醫(yī)院前的海岸向我揮手,原來是為了這個原因。……我笑著說:“不要緊。我站立的地方距懸崖邊還有六尺遠(yuǎn)哪!”
“真的?從醫(yī)院看去,你仿佛就站在崖邊上哪。……以為你已經(jīng)從那里下來,想不到卻蹲在這里,我想你一定又發(fā)暈了……。”
父親和我相望而笑,然后一道向醫(yī)院行去。第三天清晨,我到醫(yī)院吃早餐,平時這時候父親已起床,這天卻還沉睡未起,我頗感意外,不安地問道:“有什么不對勁嗎?”
“嗯,今早吐血了。”
父親低聲說,“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。本以為不會再有這種事了……”我非常驚訝,打開父親枕邊的陶器痰盂蓋看,里面有相當(dāng)多烏黑的血。父親不時咳嗽。每次都有少量的血雜在痰中咳出。不久,院長來診察。父親的病可能又回到以前的樣子了,我盯著院長的臉孔不放。他是剛從大@學(xué)畢業(yè)的年輕醫(yī)學(xué)士,看來頗沉穩(wěn)。
“胸部沒有什么異樣,聽不見一點空洞音。呼氣聽來雖然拖長了一點,不過這一般人也會有。”
說著,院長又查看一下痰盂。
“哦,”他說著頷首,“血色很黑,是舊血,不是剛剛咳出來的。一定是以前咳出的血蘊(yùn)積在什么地方,再咳出來的。”
父親露出很意外的表情。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“最近有沒有做過激烈的運動?”
“這個,”父親想一想,“也沒有什么特別激烈。兩星期前,曾跟M大夫(醫(yī)院里的醫(yī)生名字)一起爬山……”
“不,不是那么久以前。……總之,不要擔(dān)心,今明兩天,好好躺一躺,很快就會復(fù)原。”
院長回去了。
父母和我稍微放下心。父親遵從院長的囑咐,靜靜躺了兩天。第三天,已完全復(fù)原,又像以前那樣起床,到外頭散步。這次吐血,原因始終沒有查明,不知不覺間也就遺忘了。
父親現(xiàn)在跟我們一起住在鐮倉,健康已完全恢復(fù),比生病前肥胖,體重甚至比年輕時更重。
距那次住院已過了一年,我突然想起,父親那次吐血可能是因為看見我站在那懸崖上,憂懼得刺痛了心。院長說,是由于激烈的運動,然而縱使不是激烈的運動,過度的憂心一定也會產(chǎn)生同樣的結(jié)果。尤其像我父親這樣神經(jīng)極度敏感的人,這種事更有可能。
這么一想,更覺難過,“哦,好危險!”不安感隨之而起。我開始想到這件事的時候,自己身邊的事情似乎都驟然涌現(xiàn)在腦海中。
摘自《世界微型小說名家名作百年經(jīng)典》一書
熱門專題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