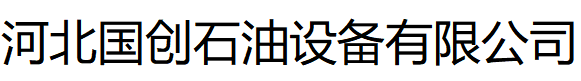我有幸成為了普林斯頓大學(xué)的學(xué)生,不幸的是,第一個(gè)學(xué)期結(jié)束,我的成績(jī)慘不忍睹,幾乎所有的學(xué)科都是D和F。教務(wù)長(zhǎng)決定把我降級(jí)為試讀生,并宣布,如果第二個(gè)學(xué)期我再有一門(mén)功課不及格,我就得卷鋪蓋走人。
第二個(gè)學(xué)期一開(kāi)始,我就強(qiáng)迫自己對(duì)所選修的學(xué)科產(chǎn)生興趣。其中,我選修的一個(gè)學(xué)科叫做“核武器戰(zhàn)略及軍備控制”,每周三個(gè)學(xué)時(shí)。一個(gè)周一的早上,著名物理學(xué)家弗里曼·迪森在課堂上跟大家討論原子彈的問(wèn)題:“原子彈的威力大家都知道,這在日本的廣島和長(zhǎng)崎也已經(jīng)得到證明。你們說(shuō)原子彈的威力這么大,那么制造一枚原子彈到底需要多少原料呢?”
全班沒(méi)有一個(gè)人回答。
迪森教授一笑,繼續(xù)說(shuō):“各位都知道,制造原子彈的重要原料是钚。要制造一枚低級(jí)的原子彈僅需15磅的钚。如果增殖反應(yīng)堆被廣泛應(yīng)用,那么每年運(yùn)送到美國(guó)的钚可以制造出幾千枚原子彈。這些钚很有可能被盜走或在運(yùn)輸途中被劫走。”
很多同學(xué)馬上說(shuō),這樣的話,恐怖分子豈不可以自制原子彈?
“不可能!”一個(gè)同學(xué)反駁道,“恐怖分子沒(méi)有制造原子彈的技術(shù)。再說(shuō),他們也無(wú)法得到資料。”
不可能?還是有可能?這個(gè)問(wèn)題開(kāi)始在我的腦中揮之不去。我查閱了參考書(shū),結(jié)果發(fā)現(xiàn):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學(xué)家說(shuō),恐怖組織可以輕易地從核反應(yīng)堆盜取钚或鈾,然后運(yùn)用已經(jīng)公開(kāi)的資料設(shè)計(jì)出可以引爆的原子彈,而且,除了钚之外,別的所有材料都可以合法地從五金商店或者化工公司買(mǎi)到。
突然,一個(gè)念頭在我的腦中蹦了出來(lái):像我這樣連中等水平也算不上的物理系的學(xué)生能夠設(shè)計(jì)出一枚理論上可以引爆的原子彈嗎?如果成功的話,我相信教務(wù)長(zhǎng)肯定不會(huì)讓我退學(xué)了。我決定去請(qǐng)求弗里曼·迪森教授做我的導(dǎo)師。
“我可以給你指導(dǎo)。但是,你要明白,我參與的是政府的機(jī)密工作,任何絕密資料我都不能說(shuō)給你聽(tīng),我能給你提供的資料只能是在學(xué)校的圖書(shū)館查到的。還有,由于涉及政府的機(jī)密,所以凡是有關(guān)原子彈的設(shè)計(jì)的問(wèn)題,我既不能回答‘是’,也不能回答‘不是’。”迪森教授淡淡地說(shuō)道。
“是的,先生。我明白。”我答道。
幾天后,迪森教授交給我一張書(shū)單。我興奮極了,但一瞧上面所列的書(shū)目,馬上感到失望。他列的都是一些普通核物理和當(dāng)代原子理論方面的書(shū)籍。這些都是一般原理的教科書(shū)嘛!我原本還指望他能給我多一點(diǎn)指導(dǎo)呢!
隨后,迪森教授也只向我解釋核物理的普通原理。如果我問(wèn)及具體的設(shè)計(jì)或者數(shù)據(jù)時(shí),他就會(huì)掃一眼我的圖紙,然后把話題岔開(kāi)。剛開(kāi)始時(shí),我以為他這樣做是默認(rèn)我做對(duì)了。為了確認(rèn)這一點(diǎn),我給了他一個(gè)錯(cuò)誤的數(shù)據(jù)。結(jié)果,他看過(guò)后,又岔開(kāi)話題。
一個(gè)月后,我去了趟華盛頓特區(qū)。我聽(tīng)說(shuō)那里有一份已經(jīng)解密的核工程文獻(xiàn)。果真,我找到了那份詳細(xì)描述20世紀(jì)40年代初期最前沿的科學(xué)家都知道的原子裂變的細(xì)節(jié)的文獻(xiàn)。
當(dāng)我把那份文獻(xiàn)放到迪森教授面前時(shí),他的表現(xiàn)很震驚。這讓我確信,我肯定可以拿出一個(gè)有價(jià)值的方案來(lái)。
要引爆一枚原子彈需要很多精確的配置材料,這些材料多數(shù)是如何引爆反應(yīng)堆保護(hù)層外圍的炸藥。這些不同的炸藥的排列則是制造原子彈的最高機(jī)密。而這也是我需要攻克的最大的難題。
接下來(lái)的三個(gè)星期,我什么課都不上了。我不分晝夜地干著。我從一個(gè)恐怖分子的角度去思考每一個(gè)問(wèn)題:這枚原子彈的造價(jià)不能太昂貴,設(shè)計(jì)要簡(jiǎn)便,而且體積要小,小到能裝進(jìn)汽車(chē)的后備箱。
我的設(shè)計(jì)實(shí)質(zhì)上是在拼湊一個(gè)復(fù)雜的七巧板游戲。我每天都在瀏覽文件,尋找尚未解密的知識(shí)領(lǐng)域。一旦解決了那個(gè)板塊,我就馬上拼湊上去。
離第二個(gè)學(xué)期結(jié)束還有三周,這個(gè)“七巧板”還差兩塊沒(méi)拼好。一是要使用那些炸藥,二是這些炸藥應(yīng)該如何圍繞钚排列。又一周過(guò)去了,這兩個(gè)問(wèn)題沒(méi)有取得絲毫進(jìn)展。我不得不重新審查我的整個(gè)設(shè)計(jì)過(guò)程。哦,上帝,原來(lái)有幾個(gè)數(shù)據(jù)被我計(jì)算錯(cuò)了。www.lizhidaren.com
還有10天時(shí)間,我又審查了一番整個(gè)設(shè)計(jì)過(guò)程。如果我的化學(xué)方程式正確,我的這枚原子彈的威力不會(huì)比投放廣島與長(zhǎng)崎的那兩枚差。但是,我必須了解要使用的炸藥的性能。
學(xué)期結(jié)束倒計(jì)時(shí)第9天上午,我打電話給杜邦公司(美國(guó)大型化學(xué)公司,譯者注),找到了化學(xué)炸藥部經(jīng)理格拉夫斯。
“您好,格拉夫斯先生。我是普林斯頓大學(xué)物理系的一名學(xué)生。我正在研究在一個(gè)球形的金屬體內(nèi)放置某種極高密度的炸藥的排列問(wèn)題。您能給我建議一種符合這一要求的杜邦公司的產(chǎn)品嗎?”我開(kāi)門(mén)見(jiàn)山地說(shuō)。
“當(dāng)然可以。”他愉快地說(shuō)道,“就您說(shuō)的這種情況,我們公司的產(chǎn)品完全可以解決這樣的密度問(wèn)題。”
我順利得到了急需的信息。
學(xué)期結(jié)束倒計(jì)時(shí)第8天下午,我拿著寫(xiě)好的論文直奔物理系大樓,闖入系主任的辦公室。系主任停下手中的工作,像看怪物一樣地看著我。我已經(jīng)一個(gè)月沒(méi)有刮臉了。
“我有一篇論文想讓您看看。”我說(shuō)。
學(xué)期結(jié)束倒計(jì)時(shí)第5天上午,我再次來(lái)到物理系主任辦公室。系主任卻不在,我的論文也不見(jiàn)了。
“你是設(shè)計(jì)原子彈的那個(gè)學(xué)生吧?”秘書(shū)問(wèn)我。
“是的。”我答道。
“系領(lǐng)導(dǎo)已經(jīng)開(kāi)過(guò)研討會(huì),打算把你的論文作為保密項(xiàng)目交給美國(guó)政府。”秘書(shū)盯著我說(shuō)道。
我差點(diǎn)兒沒(méi)暈倒。好一會(huì)兒,我不知說(shuō)什么,但心里響起一個(gè)聲音:“我想我不會(huì)被退學(xué)了。